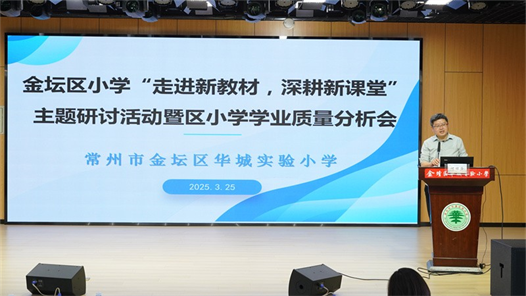发布时间:2017-12-12 信息发布:无 浏览量:2677次
试谈中学作文教学中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顾黄初
学和用──内容和方法问题
学习任何东西,目的总是为了要掌握它,运用它,发展它。所以,谈作文教学,首先要谈学和用的问题。
作文教学里面的学和用,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学什么才真正有用,这是学习内容问题;二是怎样学才真正管用,这是学习方法问题。
从作文课的学习内容看,历史的答案或者时代的要求似乎是这样:作文教学应该让学生学会写种种实用的文章。什么是实用文章?不同时代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在封建时代,要学生学奏章传记、诗词歌赋诸体文,认为这些东西是“实用”的。梁启超、蔡元培等人不主张学写这样一类东西,提出中学生应该学习写作“实用文”。当时他们心目中的“实用文”,主要是指一般记事论理的记载文和论辩文。梁启超还特别要求学生读一些清代考据家的文章,让他们学会搜集有关资料来阐发一种见解的本领。后来夏尊、叶圣陶等人,在记载文中特别把说明文提了出来,强调要学生学会写记叙性、说明性、议论性的一般文章。 叶圣陶 先生几十年来始终坚持这一主张,直到现在,他还一再提醒在中学里要让学生少做那些文艺性或抒情性的散文体、小说体,多做一些为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所必需的实用文章。这是适应治学的需要。 黎锦熙 先生主张要让学生多写“修养日记”和“读书札记”,前者记自己的生活感受,后者写个人的学习心得。这都是从实用出发的。
今天,20世纪80年代的青少年,他们是四化建设的后备军,他们今后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究竟需要学会写一些什么样的文章才合乎时代的需要呢?这个问题似乎需要通过调查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回答。
随之而来的是学习方法问题。既然学的是实用性的文章,那么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在实际运用中来学习,即在用中学。当然,这里的“用”不同于今后在实际生活中的“用”。学校中的“用”多半是假设性的“用”。所谓设计教学、情境教学,它们在作文课中的应用,实际上就是力图安排一种假设性的情境来培养学生写作某类文章的能力。日本近年来特别强调要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进行作文训练,正是为了要纠正过去“为作文而作文”的偏颇,使作文训练尽可能地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现在,让作文训练同实际生活尽可能接近的想法和做法,已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同志所理解并接受,这是一个极好的兆头。由此发端,中学作文教学有可能开创出新局面来。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说中学作文教学应该重视实用文章的训练,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抛弃那些在多数人看来未必有多少“实用”价值的文艺性、抒情性文章的训练。所谓“实用”,应该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从培养青少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角度看,活跃学生的思想,陶冶学生的情操,发展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丰富学生的想象联想能力,激发学生讴歌一切美好事物的强烈愿望等等,都是具有“实用”意义的。所以,在中学阶段,特别是初中阶段,写些形象地反映生活、讴歌生活的带有鲜明主观色彩的文章,还是必要的,应该有计划、有目的地加以训练;缺少了这一个组成部分,整个教学内容就不完整。所以,在学和用的问题上,也要防止任何片面性。
虚和实──材料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语文教学战线上的人们纷纷提出要指导学生说真话,写真情。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但有人认为:中学生的生活十分单纯,接触面也有限,作文可以容许虚构。意见有了分歧,争鸣文章甚至上了《人民教育》。这个作文材料上的虚实问题,究竟该怎样理解才是呢?
研究前辈们的理论观点和国外一些学者的见解,答案似应是这样:学生作文主要应该求“实”,但也容许必要的、合理的“虚”。
考察人们的写作实践,反映生活的方式方法不外乎三种:如实地反映、虚拟地反映和虚实结合地反映。中学生从总体上说,绝大多数是未来的实际工作者和科技人员,他们更多地需要掌握如实地反映生活、如实地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的技能。因此,强调要中学生写真人实事和真情实感,强调在作文课上要训练学生学会写日记、调查报告、读书札记、实验总结、资料综述、科技说明、科技论文、访问记、参观记这类实用文章,在训练过程中培养学生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的好作风,这确实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感受还十分肤浅,还有待于在实践中加深理解。
但是,中学生毕竟是处在思维能力需要多方面加以培养、发展的重要时期,过早地把他们的思维拘囿于单纯“写实”的范围之内,也未必妥当。国外有些语文教学研究工作者认为,“一切作文在某种程度上都要依靠学生的创造性想象”。这话是很有道理的。记叙性、抒情性的文章,需要有创造性想象,这容易理解;那么说明性、议论性的文章呢?需要不需要想象、联想,甚至幻想?郭老说,科学也需要幻想。可见,形象思维需要想象和联想,逻辑思维也有它特殊的想象和联想。试想:议论中如果没有联想就很难创造性地运用类比推理;没有想象,假言判断和假言三段论有时也会失去光彩和魅力。因此,在指导学生作文的时候,一方面固然要注意培养学生科学的求实精神,让他们懂得记事论理都应该言必有据,实事求是;另一方面也要引导他们展开联想和想象的翅膀,对写作材料进行必要的剪裁调度和加工处理,以便更好地表现主题、抒发感想或揭示事物本质。而这种想象、联想,其本质还是实的。
这样看来,学生作文的材料也可以有三种情况:全部真实的,部分真实的,全部虚构的。有些作文,比如写人物传记、家庭小史、家乡风貌以及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实验报告、调查访问记等等,都必须是真实可靠的。一些议论性的作文,也必须句句出自内心,不能言不由衷。有些作文,比如根据假设的情境来写的各种文章以及提供材料要求扩写、改写和续写的文章,就不能不采用虚实结合的方法,用许多想象出来的材料来结撰成文。至于记叙文中对真人真事进行必要调整、加工,只要不违背生活逻辑,又为表达主题所必需,也应当容许;只是要求在文末附上“小注”,说明什么地方是虚构、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虚构。这样做,既便于教师批阅时评判优劣,也有助于作者本人养成严肃地对待写作的良好作风。此外还有一些作文,比如童话和科幻小品等,就全属虚构的了。这类作文过去我们重视不够,是个缺陷。 叶圣陶 先生早年在论及发展儿童身心的时候,曾提到过要充分给儿童以幻想的天地。他自己的童话作品就曾经影响和滋育过几代人。最近,人民教育出版社刘国正同志以他诗人特有的感情和体验,也重新提出了写幻想材料的问题。看来,在作文教学中适当布置一些幻想性的命题,也还是完全必要的。
多和少──数量问题
作文训练的量,确实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特别是过去一段时间,各科教学都有追求“大运动量”的趋势,作文训练也不例外,据说最多的竟达到每学期写大小作文四五十篇之多。这样做的结果是师生都感到不胜重荷。可见,想以“多”取胜,是要事与愿违的。那么,究竟该怎样恰当限定作文训练的量呢?主张作文次数以“多”为好的同志,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多读多写”,一直被公认为是语文教学的一条传统经验;大纲上也要求教师尽可能地给学生以更多的练笔机会。可见,多写一些有好处。问题在于,当我们强调“多”的时候,要不要把“需要”与“可能”、“数量”和“质量”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加以考虑,使规定的数量能符合学校教育的客观规律。
回顾近代中国的语文教学史,许多有识之士对一味追求读写数量的传统做法早已表示过怀疑。因为按照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客观规律,多实践多操作就会形成某种技能技巧这种“实践出真知”的道理,虽普遍适用于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一切方面,但从学校教育这种人类发展自己的特殊手段来说,只满足于“多”字,只要求以“多”取胜,而不强调按科学规律办事,不要求用一种符合人们认识规律的科学方法在一定时间内迅速有效地把知识、技能传授给学习者,那就无异于取消教育。所以,真正理解教育的特殊功能的人,对此表示怀疑是理所当然的。这里且举梁启超为例。梁启超是反对只讲“多写”而不讲“实效”的。他主张,在篇数上,与其做得多而草率应付,使师生都感到疲于奔命,倒不如少做几篇,抓细抓实,让学生做一篇有一篇的收获。所以,从实质上看,梁氏主张的“少”倒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多”。此外,他还主张在课外要指导学生随意做“笔记”,读书笔记、听课笔记、写作笔记都可以,根据各人需要自己酌定,以此作为课内命题作文的必要补充。因此,严格地说,梁氏对作文训练的量是要求:重点作文反复写,随感笔记经常写,使二者互相配合,相辅相成。这在写作总量上仍是“多”的而不是“少”的,但这个“多”多得较为符合教学规律,因而收效可能比单纯追求篇数之多要好些。
黎锦熙 先生对于语文教学曾提出过这样三句话:“写作重于讲读,改错先于求美,日札优于作文。”在他看来,一般综合性的作文训练,次数宜乎少些,每作必求有切实的收效;而片断性的练笔,特别是日记、笔记之类,则尽可能鼓励学生自觉地多做,并养成习惯,使练笔与练文、精练与多练结合起来。这种观点同梁启超基本一致。
综观前辈们的一些见解,我以为,在作文训练的数量上,在初中阶段课内作文不妨稍多些,但也不宜多于每两周一篇;同时配之以课外自由练笔的指导。随着学年的递升,课内作文的篇数可以逐渐减少,而对这有限的几次训练,必须要求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充分准备、过细推敲、反复修改,实行一题多作或一作多改,务求做一篇有一篇的收获;同时给学生以更多的自由练笔的机会。这样做,也许可以在不增加学生过重负担的情况下真正提高作文教学的效率。
深和浅──程序问题
作文教学应该依循一个合理的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这在目前已是大家共同的认识。但究竟怎样的程序才算合理,才算科学,才比较地容易收效,各人的看法和体会却不一样。
一般地说,教学的程序应体现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的原则。采用传统的命题作文方式,就不容易分出前后程度的深浅来。“我的老师”这个题目,小学里可以用,中学里可以用,大学里也可以用。大作家冰心、魏巍还用这个题目写成了脍炙人口的散文。同样的命题,写出的文章深浅繁简可以大不一样。所以,教学内容的深浅主要应该体现在训练的要求上面。规定分阶段训练项目的质量要求,就构成现在所谓的训练序列。
稍稍留心一下中学作文教学的现状,可以知道当前人们正在探索的有这么三种主要的序列设计原则:一是以文体为序,二是以知识为序,三是以能力为序。在这三种原则下,又有若干不同的排列方法。
历史较久的是以文体为序的原则。梁启超在这方面贡献较突出,他可以说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按照教学需要对文体进行合理分类和合理排列的第一人。梁氏曾把一般文章分成记载文和论辩文两大类,他主张“最好每年前学期授记载文,后学期授论辩文,年年相间”。在这两大文体中,他认为还应该按照由浅入深、由易入难的要求细分若干小类,“例如记载文先授记静态者后授记动态者。动态之中先授一人或少数人一时或短时的动态,最后才授许多人许多时的动态。论辩文先授倡导一类,次授考证质驳批评等类。各类中先授单纯问题的论辩,最后才授复杂问题的论辩”。梁氏这种设想,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科学根据的,也符合文章写作由易到难的一般规律;缺陷是过于粗略。同时,一个学期集中训练一种文体,不仅单调,也不利于全面培养学生各种思维能力。但是,他的这些创见却对至今为止的语文教学都有影响。以后夏尊、叶圣陶诸位前辈在论述作文教学问题时都程度不同地吸取了梁氏的许多有价值的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到现在,这种按文体为序的作文训练体系已派生出这样三种主要类型:一是大体因袭梁启超当年的做法,分文体集中训练,初中先记叙,再说明,后议论,高中先复杂记叙,再复杂议论;二是分文体有重点地穿插训练,每学期三大文体“全面出击”,但初一以记叙为重点,初二以说明为重点,初三以议论为重点,高中同例;三是分文体单项训练,把每种文体的写作要领排成一系列训练项目,逐项进行训练,中间有计划地安排若干次综合性作文,做到单项训练与综合训练的结合。
其次是以知识为序。这在国外已开始流行,但在我们国内却还只有少数同志在做局部的试验。写作是离不开语言的。如果把学语言同学写作结合起来,也许可以开拓出一条作文教学的新路来。现在一般讲授语言知识的书,大都按照字──词──句──篇的次序编列内容,中间缺了“段”这一环节,而从语言运用的实际情况来看,“段”倒应该是文章中表述一个完整意思的基本单位。国外有些写作教材就是按选词──造句──构段──谋篇这样四个环节来指导学生进行训练的。过去,夏尊等人在撰写《文章作法》时曾经部分地接触到这些问题,可惜当时没有充分展开,没有深入下去。最近我们国内已开始有人在研究“段”的性质、特点和表述功能;对于“句”在实际运用中种种变化规律,也在进行探索,并有了初步的成绩。这些研究工作,对今后的作文教学无疑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再次是以“能力”为序。“能力”本身是一个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和分类的概念。目前,以“能力”为序的作文训练体系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观察──分析──表达”的三阶段训练体系;一种是“搜集材料──整理材料──书面表达──文章修改”的四阶段训练体系;另一种是“审题──立意──选材──布局──表达(又分若干细目)──修改”的多阶段训练体系。今后,随着教育学、心理学、文章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工作不断地深入,以“能力”为序来设计作文训练的内容、项目和步骤,也必将出现更多更新的创造性成果。
就当前我国中学作文教学的实际状况而论,当务之急似应是设计出一种大面积上的师生都可能接受和便于应用的作文训练程序来。作文教学所要解决的无非是“写什么”和“怎么写”两大问题。“写什么”,粗略地分,不外乎写事、写人、写物、写景、写情、写理。单纯的是:一事、一人、一物、一景、一番情、一种理;复杂起来是:一事多人、一人多事、多人多事、由物及人、事物组合、事物关系、托物言志、触景生情、事物剖析、事理推究、驳诘辩难等等。“怎么写”,涉及到写作上的各种技能技巧,头绪比较复杂,不容易单线条地勾出其由浅入深的层次,但大体上还是可以从三条线上理出一些项目来的。这三条线是:写作的基本能力(即审题、立意、选材、剪裁、布局、表达、修改等能力);思维的基本能力(即观察、分析、综合、概括、推断、想象、联想等能力);驾驭各种文体的基本能力(即掌握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以及其他应用文的各种写作要领)。如果以“写什么”为经,以“怎么写”为纬,把有关“怎么写”的三个主要方面所列出的若干训练项目穿插着编排起来,也许可以形成一个纵横交织、循环加深、循序渐进的训练程序来。而这样的程序,在目前可能比较容易被多数同志所接受。
评和改──过程问题
作文的批改,牵涉到教学的指导思想,牵涉到整个作文训练的着眼点问题。
叶圣老一贯强调,在作文课上必须培养学生自己修改文章的能力。这是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过去我们讨论作文批改问题,总是着眼在教师的批改如何才能节省时间、如何才能减少无效劳动、如何才能不挫伤学生积极性等等,却很少去研究怎样才能逐步提高学生自批自改的能力。原因就在于指导思想还不十分明确。
如果我们真正意识到作文训练的着眼点应该放到培养学生自能作文、自能改文上来,那么前辈们有两条经验就很值得我们重视:一是教师只加批语,或只加批改符号,发下去让学生自行修改,改后再评分。在现代语文教学史上,首创符号批改法的大概是 刘半农 先生。而 黎锦熙 先生关于“改错先于求美”的主张,其精髓就在于要求学生自己知错改错,而不是教师捉笔代庖,所以他也提倡符号批改法。第二是师生共同批改。具体做法很多。 王力 先生曾经介绍经验说,他自己在大学预科担任国文课时采用过黑板上公开批改作文的做法,事先选择一篇有代表性的习作抄录在黑板上,然后师生共同讨论,逐句评改。这是一种“手把手”教的好方法。在师生共同批改方面做得较为彻底的当推 于在春 先生,他在30年代曾经试验过一种称之为“集体习作”的做法,从命题到材料的搜集整理,到确定提纲,到最后落笔成文,都经过师生共同讨论、商定。这种教法,其着眼点正在于要教会学生自能作文、自能改文,与叶圣老的观点一致。近年美国有所谓“商议教学法”的试验,基本精神同在春先生四十多年前的做法近似。当然,这种做法有烦琐的一面,实行起来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适当变通;但不管怎么说,师生共同活动的方式在讲读课上已经创造了许多新经验,而在作文课上至今似乎还没有多少进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辈们的开辟工作还是值得珍视的。
《扬州师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4年04期
昨天访问: 226675 | 今天访问: 261723 | 本月访问: 261723 | 上月访问: 10859587 | 访问总数: 267717946
Copyright® 2019-2024 金坛教育服务 苏ICP备06023074号